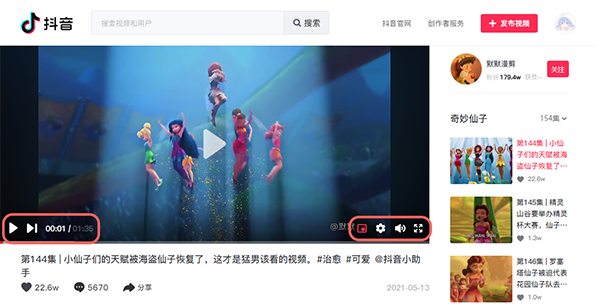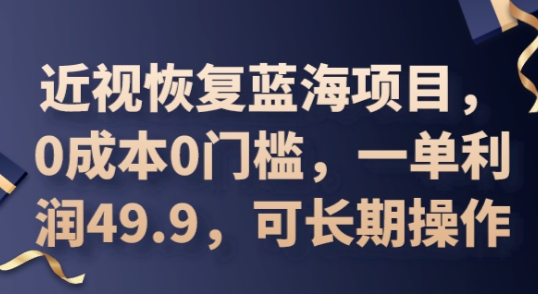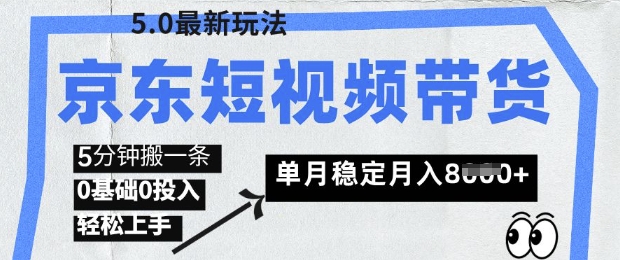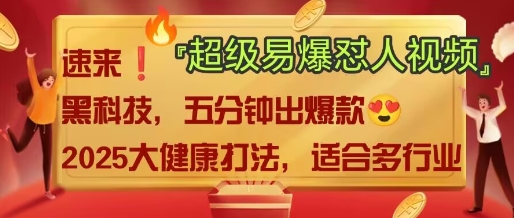说到生物学,脑海中浮现的几个重要议题常常难以回避。对于我们这些对生物学领域稍显陌生的人来说,最为熟悉且容易想到的莫过于“生命进化”和“DNA双螺旋结构”。
“生命进化”无疑是由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并发表的理论。这一理论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生命起源和多样性的认知,成为生物学领域的基石之一。
而“DNA双螺旋结构”则在目前的普遍认知中被归功于詹姆斯·沃森、弗朗西斯·克里克以及莫里斯·威尔金斯这三位科学家的发现。
然而,有趣的是,这三位科学家在向世人介绍这一发现时,似乎都意外地淡化了第四个人的存在。这种巧合使得这一伟大发现留下了一些神秘的色彩,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研究幕后故事的好奇心。
——罗萨琳•富兰克林。
罗萨琳·富兰克林
罗莎琳·富兰克林生于伦敦,成长在一个富裕而在政治和学术方面都取得显赫成就的犹太家庭。尽管出生在这样一个条件优越且政治底蕴深厚的家庭,年幼的罗莎琳并没有走上一般人期望的千金小姐的道路,选择嫁给有地位的绅士。相反,她从小就怀揣着成为一名科学家的梦想。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尽管女性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却并不被认为有资格获得学位,这类似于我国民国时期,女性上大学更多是为了提升婚嫁的筹码。
尽管罗莎琳的决定遭受了她父亲的反对,后者认为“女孩子只需找份平稳的工作,顺顺利利嫁人即可。”然而,罗莎琳并未受父亲言论左右,以出色的表现毕业于剑桥大学。然而,可惜的是,当时的剑桥大学并不授予女性学位,因此罗莎琳实际上只拥有一个“名义上的学位”。
1945年,凭借一篇题为《固态有机石墨与煤和相关物质的特殊关系之物理化学》的论文,罗莎琳终于获得了她的物理化学博士学位。自1945年战争结束以来,她发表了多篇关于煤炭的研究论文,同时学习X射线晶体衍射技术,这些成就使得罗莎琳在国际学术界声名鹊起,并于1950年受聘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然而,正如中国古谚所言,“福祸相依”,在这一阶段,罗莎琳遇到了她科研成果被窃取的第一个“小偷”——莫里斯·威尔金斯。
抵达国王学院后,罗莎琳加入了由物理学家约翰·兰道尔主持的研究组,投身于DNA结构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当时莫里斯·威尔金斯在DNA领域没有显著的研究成果,兰道尔曾写信明确指出只需要罗莎琳一个人完成研究。
然而,威尔金斯当时正在度假,声称没有看到这封信。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真的看到了信件,但在威尔金斯回到国王学院后,可能是出于对女性的歧视或者是因为罗莎琳抢走了他的工作,他对罗莎琳十分反感,经常贬低她,并拒绝与她分享之前的研究成果。
作为一名合格的研究员,威尔金斯本可以选择结束当前的DNA研究,寻找其他研究方向,或者将罗莎琳视为合作伙伴,共享研究成果。然而,他两者都未选择,而是走上了第三种道路,独自保留成果,将自己的研究与罗莎琳的研究划清界线,形成明确的分割。
在威尔金斯率先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罗莎琳当然不会退让,她独自开始了对DNA的深入研究。然而,威尔金斯并非仅仅在理论上划定了分界线,他还经常干扰罗莎琳的研究,要求她公开研究成果。因此,两人对彼此都不怎么满意,矛盾在这里埋下了伏笔,尽管暂时还能勉强相处。
时间飞逝,转眼到了1951年11月,罗莎琳与那两位“小偷”再次相遇的时刻即将到来。这一时期,罗莎琳提出了A型DNA的X射线衍射图,为DNA研究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随后在剑桥大学进行了一场重要的演讲。
在这个时候,詹姆斯·沃森刚好在由威廉·劳伦斯·布拉格主持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研究蛋白质结构。得知这些信息后,沃森与克里克开始着手排列DNA的螺旋结构,当时他们提出的模型是三股螺旋的。
沃森与克里克曾邀请罗莎琳、威尔金斯和葛林斯参观他们的三股螺旋结构模型。罗莎琳在审视这些模型后,本着科学家的严谨态度提出了许多批评,尽管这些批评可能听起来不那么讨人喜欢。由于这些批评,沃森与克里克被他们的上司布拉格要求停止DNA结构的研究。
罗莎琳对他们研究的批评让他们被迫停止,这表明当时罗莎琳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受到广泛认可,可以说她在科学界是一位杰出的学者。
然而,仅仅因为这次批评,沃森在他的著作《双螺旋》中将罗莎琳·富兰克林刻画成一个典型的西方“女巫”形象。这种描绘几乎是对这位为他们的研究提供必要条件的研究员进行全方位的诋毁。更令人不解的是,沃森将罗莎琳的科研地位描述为威尔金斯的“助手”(打杂的),尽力压低了她在这一研究中的地位。
这是否与沃森对女性的厌恶有关,还是仅仅是他个人对罗莎琳的反感?当时我们无法了解他的内心想法,但我们能够确认的是,从这件事看,沃森绝对不是一个在人格和品德上值得尊敬的人。
这场演讲在当时没有给罗莎琳的生活带来任何波澜,她继续专注于自己的研究。然而,变故发生在两年后,即1953年。由于罗莎琳受到女性歧视的困扰,她拒绝向沃森和克里克提供数据。然而,由于威尔金斯对女性的歧视和对罗莎琳的厌恶,他擅自将罗莎琳的研究成果交给了沃森和克里克观看。
正是在这一年,三篇论文于4月25日同时发表。沃森与克里克首先发表,接着是威尔金斯等人,最后是罗莎琳。沃森与克里克在论文中提到受到威尔金斯和罗莎琳等人研究的启发,但没有详细说明,也没有表示感谢。
在论文结尾不敢表达感谢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威尔金斯和心情复杂的罗莎琳只能在论文中陈述自己的数据与沃森和克里克的模型相一致。
然而,不幸的是,1958年,罗莎琳,一位长期从事放射性射线研究的科学家,年仅37岁就患上癌症,离世。
1962年,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凭借他们的DNA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网络上阅读资料时,我发现很多软文写道:罗莎琳并不在乎,甚至微笑着面对研究成果被窃的事情,并表示:“你们拿去用了?那很好!”
我并没有亲眼见过罗莎琳,也不知道她是否真的不在乎,但我猜测,她是在乎的。
研究成果就像是一部被盗的文学作品、一首被抄袭的歌曲,只是因为当时对女性的不友好,使得罗莎琳的声音被镇压。
然而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无法知晓,那些泛黄的历史记载早已随着时间飘散,而作为科学家的罗莎琳或许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并未对此过分计较。但是,从沃森对罗莎琳的贬低来看,我们又怎能原谅一个窃贼?甚至在罗莎琳离世后,他仍然未放弃对罗莎琳——她的核心研究导师的诽谤。
我们无权原谅沃森,这是罗莎琳的权利。然而,我们有责任铭记这段历史,因为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记忆。遗忘历史就等于背叛自己。
亲,推荐开通本站超级会员,全站资源全免费(每日持续更新)